钉钉更新7.7.0版本 多维表全面免费
钉钉更新7.7.0版本 多维表全面免费
钉钉更新7.7.0版本 多维表全面免费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jìzhě) 马纯潇 杜春娜
 在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是(shì)分性别的(de)。当所指群体中男女都有的时候(shíhòu),一般都称作“他们”而非“她们”。但是如果是在4750年的广饶傅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对男女混杂的群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她们”,因为科学家们刚刚(gānggāng)确认,这时期的傅家遗址处于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
这是世界上(shàng)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由此(yóucǐ)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科学确认的(de)母系社会。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也正因其(qí)重要,科研成果被著名的《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那么,“她们”是如何被发现的(de)(de)?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是如何得到考古学实证的?记者对参与这项重要研究(yánjiū)的专家们进行了采访。
在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是(shì)分性别的(de)。当所指群体中男女都有的时候(shíhòu),一般都称作“他们”而非“她们”。但是如果是在4750年的广饶傅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对男女混杂的群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她们”,因为科学家们刚刚(gānggāng)确认,这时期的傅家遗址处于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
这是世界上(shàng)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由此(yóucǐ)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科学确认的(de)母系社会。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也正因其(qí)重要,科研成果被著名的《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那么,“她们”是如何被发现的(de)(de)?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是如何得到考古学实证的?记者对参与这项重要研究(yánjiū)的专家们进行了采访。
 傅家遗址历年(lìnián)发掘位置图
“母系社会”真的存在(cúnzài)吗
母系氏族社会(huì)到底存在(cúnzài)不存在?你要这么问,估计连中学生都会笑话你:“肯定存在呀,课本里写着呢”。没错,中学课本里说(shu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chūxiàn)了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shì),课本里写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未得到过考古学的实证。直到6月4日,这一尴尬局面才不复存在。
山东省文旅厅(wénlǚtīng)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kǎogǔ)(kǎogǔ)研究院院长孙波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此前曾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过长达近30年的(de)一线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孙波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母系社会理论的形成(xíngchéng)和发展过程。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zài)《母权论》(1861)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nián)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qīnshǔchēngwèi)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构建了(le)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ēngésī)(ēngésī)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qǐyuán)》一书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gòngchǎnzhǔyì)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为指导开展(kāizhǎn)了大量针对(duì)史前(shǐqián)社会组织的复原和(hé)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yǎngsháowénhuà)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rénlèixué)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现代民族学(mínzúxué)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bèi)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shǐ)研究人员(rényuán)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shíxiàn)对古代人类(rénlèi)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yǔ)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zǔzhī)体系(tǐxì);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成为(chéngwéi)困扰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无意之间成为了破局者。
傅家遗址历年(lìnián)发掘位置图
“母系社会”真的存在(cúnzài)吗
母系氏族社会(huì)到底存在(cúnzài)不存在?你要这么问,估计连中学生都会笑话你:“肯定存在呀,课本里写着呢”。没错,中学课本里说(shu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chūxiàn)了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shì),课本里写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未得到过考古学的实证。直到6月4日,这一尴尬局面才不复存在。
山东省文旅厅(wénlǚtīng)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kǎogǔ)(kǎogǔ)研究院院长孙波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此前曾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过长达近30年的(de)一线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孙波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母系社会理论的形成(xíngchéng)和发展过程。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zài)《母权论》(1861)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nián)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qīnshǔchēngwèi)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构建了(le)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ēngésī)(ēngésī)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qǐyuán)》一书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gòngchǎnzhǔyì)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为指导开展(kāizhǎn)了大量针对(duì)史前(shǐqián)社会组织的复原和(hé)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yǎngsháowénhuà)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rénlèixué)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现代民族学(mínzúxué)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bèi)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shǐ)研究人员(rényuán)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shíxiàn)对古代人类(rénlèi)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yǔ)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zǔzhī)体系(tǐxì);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成为(chéngwéi)困扰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无意之间成为了破局者。
 昝金国(jīnguó)(左四)在2021年傅家遗址发掘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者,源于他们对广饶傅家遗址时间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调查(diàochá)和发掘(fājué)。
傅家(fùjiā)遗址位于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de)中部。遗址东距淄河约3公里(gōnglǐ),北距小清河约12公里。从遗址向东约200米是东辛公路,潍高公路从遗址中部东西穿过。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dàwènkǒu)文化(wénhuà)遗址。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总面积(zǒngmiànjī)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duījīcéng)厚约3米,内涵丰富。
尽管苹果砸头促使牛顿发现(fāxiàn)(fāxiàn)万有引力的传说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奇心(hàoqíxīn)是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最大驱动力。考古学也不例外。傅家遗址的墓葬就引发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极大好奇心。
孙波很早就关注到傅家遗址的(de)墓葬(mùzàng)与其他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不太一样,“排列非常紧密,感觉像超越了血缘关系。我曾经猜测(cāicè)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原因到底(dàodǐ)是什么,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孙波当然不会靠猜测,他在等待时机寻找答案。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对(duì)傅家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务办(bàn)主任、副研究馆员昝金国担任这次发掘项目(xiàngmù)负责人。他在发掘中同样被傅家遗址的“不一样”所困扰。“这里墓葬(mùzàng)的布局、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以及墓主的头向,与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都有很大(hěndà)差别。”
对于学者来说,遇到问题当然就要解决,可是解决傅家遗址的“不一样”,单靠传统(chuántǒng)的考古学似乎已经力不从心。“考古学的发展(fāzhǎn)日新月异,现在(xiànzài)只靠原来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yánjiū)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孙波说,“我们需要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rénlèixué)等(děng)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联合研究。也(yě)正是这次联合,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母系社会第一次被我们用考古学的材料证实了。”
昝金国(jīnguó)(左四)在2021年傅家遗址发掘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者,源于他们对广饶傅家遗址时间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调查(diàochá)和发掘(fājué)。
傅家(fùjiā)遗址位于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de)中部。遗址东距淄河约3公里(gōnglǐ),北距小清河约12公里。从遗址向东约200米是东辛公路,潍高公路从遗址中部东西穿过。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dàwènkǒu)文化(wénhuà)遗址。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总面积(zǒngmiànjī)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duījīcéng)厚约3米,内涵丰富。
尽管苹果砸头促使牛顿发现(fāxiàn)(fāxiàn)万有引力的传说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奇心(hàoqíxīn)是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最大驱动力。考古学也不例外。傅家遗址的墓葬就引发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极大好奇心。
孙波很早就关注到傅家遗址的(de)墓葬(mùzàng)与其他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不太一样,“排列非常紧密,感觉像超越了血缘关系。我曾经猜测(cāicè)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原因到底(dàodǐ)是什么,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孙波当然不会靠猜测,他在等待时机寻找答案。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对(duì)傅家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务办(bàn)主任、副研究馆员昝金国担任这次发掘项目(xiàngmù)负责人。他在发掘中同样被傅家遗址的“不一样”所困扰。“这里墓葬(mùzàng)的布局、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以及墓主的头向,与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都有很大(hěndà)差别。”
对于学者来说,遇到问题当然就要解决,可是解决傅家遗址的“不一样”,单靠传统(chuántǒng)的考古学似乎已经力不从心。“考古学的发展(fāzhǎn)日新月异,现在(xiànzài)只靠原来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yánjiū)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孙波说,“我们需要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rénlèixué)等(děng)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联合研究。也(yě)正是这次联合,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母系社会第一次被我们用考古学的材料证实了。”
 宁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项目(xiàngmù)科研成果。
傅家遗址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古(gǔ)DNA技术的介入。
古(gǔ)DNA技术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为古DNA的提取非常(fēicháng)困难。根据(gēnjù)相关资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样本(yàngběn)不超过5000份。那么,傅家遗址能提取足够多的样本吗?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京大学文博(wénbó)考古学院研究院宁超。宁超生于1988年,虽说年龄还不到40岁,却是身怀绝技(shēnhuáijuéjì)。他曾在德国著名的马普所(mǎpǔsuǒ)人类历史(lìshǐ)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cóngshì)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获得了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开展联合研究的机会。
据宁超介绍,相对(duì)于(yú)南方酸性土壤来说,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tiáojiàn)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墓葬人骨标本的提取保护工作都(dōu)做得相当好,加上近年来古DNA提取技术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他的团队(tuánduì)很幸运地提取了60例古DNA样本,其中南区墓葬样本46例,北区墓葬样本14例。
那如何就(jiù)能通过古DNA测试就能判断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
“人类的DNA主要有线粒体DNA(mtDNA)和核(hé)DNA(nDNA)两种,子女的线粒体DNA来自母亲,而核DNA则是父母各贡献一半。如果一个(yígè)群体中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单倍型,是单倍体基因型的简称,在(zài)遗传学上(shàng)是指(zhǐ)在同一染色体上进行(jìnxíng)共同遗传的多个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就是若干个决定(juédìng)同一性状的紧密连锁的基因构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组发生的数量,单倍型可以指至少两个基因座甚至整个染色体。——记者(jìzhě)注)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那(nà)就能确定是来自同一母系。”宁超说,“我们的检测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宁超介绍,傅家南区44例个体共享(gòngxiǎng)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基因组(jīyīnzǔ)序列一致,而(ér)北区墓葬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确定,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zǔxiān)。
两个墓地(mùdì)各属不同的母系氏族确定了,那么这两个氏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guānxì)?“根据检测,两处墓地延续了至少250年,约10代人,且(qiě)墓地内部及墓地间存在密集的亲缘关系,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存在(chángqīcúnzài)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宁超说。
在检测中,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宁超(níngchāo)的(de)关注。他发现,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èrcìzàng),也就是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的母系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gòngxiǎng)完全相同的线粒体(xiànlìtǐ)DNA序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宁超说。
根据宁超的讲述,记者想象4750年前广饶(guǎngráo)傅家的生活场景:小霞(xiǎoxiá)是(shì)北区一位漂亮姑娘(gūniáng),她的妈妈(māmā)是氏族的首领,她每天和妈妈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劳作。一天,她看到南区一位手提猎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欢喜,向他暗施(ànshī)眼色。小伙心领神会,此后经常夜间来到北区与她相会。尽管小霞的妈妈是氏族首领,却并不会反对,因为两个氏族本来就长期通婚。不但南区的小伙会过来,北区的小伙也回到南区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但是(dànshì),无论男女多么相爱,小伙打的猎物还是要带回本氏族的。后来,小霞心爱的小伙在一次狩猎中受伤(shòushāng)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dìfāng),但是不久之后南区的人们(rénmen)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们说,这是规矩……
听了记者讲述的“浪漫故事(gùshì)”,宁超笑(xiào)了,不过他说,“这故事应该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
所谓的(de)“小霞”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她们”却的的确确(dedíquèquè)存在过。“她们”不会想到,在“她们”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会凭借(píngjiè)“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shēnghuózhuàngkuàng),并试图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shìchǎng)下载“齐鲁壹点(yīdiǎn)”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宁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项目(xiàngmù)科研成果。
傅家遗址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古(gǔ)DNA技术的介入。
古(gǔ)DNA技术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为古DNA的提取非常(fēicháng)困难。根据(gēnjù)相关资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样本(yàngběn)不超过5000份。那么,傅家遗址能提取足够多的样本吗?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京大学文博(wénbó)考古学院研究院宁超。宁超生于1988年,虽说年龄还不到40岁,却是身怀绝技(shēnhuáijuéjì)。他曾在德国著名的马普所(mǎpǔsuǒ)人类历史(lìshǐ)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cóngshì)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获得了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开展联合研究的机会。
据宁超介绍,相对(duì)于(yú)南方酸性土壤来说,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tiáojiàn)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墓葬人骨标本的提取保护工作都(dōu)做得相当好,加上近年来古DNA提取技术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他的团队(tuánduì)很幸运地提取了60例古DNA样本,其中南区墓葬样本46例,北区墓葬样本14例。
那如何就(jiù)能通过古DNA测试就能判断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
“人类的DNA主要有线粒体DNA(mtDNA)和核(hé)DNA(nDNA)两种,子女的线粒体DNA来自母亲,而核DNA则是父母各贡献一半。如果一个(yígè)群体中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单倍型,是单倍体基因型的简称,在(zài)遗传学上(shàng)是指(zhǐ)在同一染色体上进行(jìnxíng)共同遗传的多个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就是若干个决定(juédìng)同一性状的紧密连锁的基因构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组发生的数量,单倍型可以指至少两个基因座甚至整个染色体。——记者(jìzhě)注)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那(nà)就能确定是来自同一母系。”宁超说,“我们的检测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宁超介绍,傅家南区44例个体共享(gòngxiǎng)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基因组(jīyīnzǔ)序列一致,而(ér)北区墓葬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确定,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zǔxiān)。
两个墓地(mùdì)各属不同的母系氏族确定了,那么这两个氏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guānxì)?“根据检测,两处墓地延续了至少250年,约10代人,且(qiě)墓地内部及墓地间存在密集的亲缘关系,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存在(chángqīcúnzài)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宁超说。
在检测中,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宁超(níngchāo)的(de)关注。他发现,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èrcìzàng),也就是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的母系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gòngxiǎng)完全相同的线粒体(xiànlìtǐ)DNA序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宁超说。
根据宁超的讲述,记者想象4750年前广饶(guǎngráo)傅家的生活场景:小霞(xiǎoxiá)是(shì)北区一位漂亮姑娘(gūniáng),她的妈妈(māmā)是氏族的首领,她每天和妈妈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劳作。一天,她看到南区一位手提猎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欢喜,向他暗施(ànshī)眼色。小伙心领神会,此后经常夜间来到北区与她相会。尽管小霞的妈妈是氏族首领,却并不会反对,因为两个氏族本来就长期通婚。不但南区的小伙会过来,北区的小伙也回到南区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但是(dànshì),无论男女多么相爱,小伙打的猎物还是要带回本氏族的。后来,小霞心爱的小伙在一次狩猎中受伤(shòushāng)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dìfāng),但是不久之后南区的人们(rénmen)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们说,这是规矩……
听了记者讲述的“浪漫故事(gùshì)”,宁超笑(xiào)了,不过他说,“这故事应该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
所谓的(de)“小霞”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她们”却的的确确(dedíquèquè)存在过。“她们”不会想到,在“她们”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会凭借(píngjiè)“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shēnghuózhuàngkuàng),并试图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shìchǎng)下载“齐鲁壹点(yīdiǎn)”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jìzhě) 马纯潇 杜春娜
 在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是(shì)分性别的(de)。当所指群体中男女都有的时候(shíhòu),一般都称作“他们”而非“她们”。但是如果是在4750年的广饶傅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对男女混杂的群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她们”,因为科学家们刚刚(gānggāng)确认,这时期的傅家遗址处于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
这是世界上(shàng)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由此(yóucǐ)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科学确认的(de)母系社会。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也正因其(qí)重要,科研成果被著名的《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那么,“她们”是如何被发现的(de)(de)?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是如何得到考古学实证的?记者对参与这项重要研究(yánjiū)的专家们进行了采访。
在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是(shì)分性别的(de)。当所指群体中男女都有的时候(shíhòu),一般都称作“他们”而非“她们”。但是如果是在4750年的广饶傅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对男女混杂的群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她们”,因为科学家们刚刚(gānggāng)确认,这时期的傅家遗址处于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
这是世界上(shàng)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由此(yóucǐ)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科学确认的(de)母系社会。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也正因其(qí)重要,科研成果被著名的《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那么,“她们”是如何被发现的(de)(de)?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是如何得到考古学实证的?记者对参与这项重要研究(yánjiū)的专家们进行了采访。
 傅家遗址历年(lìnián)发掘位置图
“母系社会”真的存在(cúnzài)吗
母系氏族社会(huì)到底存在(cúnzài)不存在?你要这么问,估计连中学生都会笑话你:“肯定存在呀,课本里写着呢”。没错,中学课本里说(shu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chūxiàn)了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shì),课本里写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未得到过考古学的实证。直到6月4日,这一尴尬局面才不复存在。
山东省文旅厅(wénlǚtīng)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kǎogǔ)(kǎogǔ)研究院院长孙波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此前曾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过长达近30年的(de)一线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孙波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母系社会理论的形成(xíngchéng)和发展过程。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zài)《母权论》(1861)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nián)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qīnshǔchēngwèi)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构建了(le)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ēngésī)(ēngésī)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qǐyuán)》一书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gòngchǎnzhǔyì)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为指导开展(kāizhǎn)了大量针对(duì)史前(shǐqián)社会组织的复原和(hé)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yǎngsháowénhuà)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rénlèixué)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现代民族学(mínzúxué)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bèi)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shǐ)研究人员(rényuán)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shíxiàn)对古代人类(rénlèi)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yǔ)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zǔzhī)体系(tǐxì);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成为(chéngwéi)困扰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无意之间成为了破局者。
傅家遗址历年(lìnián)发掘位置图
“母系社会”真的存在(cúnzài)吗
母系氏族社会(huì)到底存在(cúnzài)不存在?你要这么问,估计连中学生都会笑话你:“肯定存在呀,课本里写着呢”。没错,中学课本里说(shu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chūxiàn)了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shì),课本里写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未得到过考古学的实证。直到6月4日,这一尴尬局面才不复存在。
山东省文旅厅(wénlǚtīng)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kǎogǔ)(kǎogǔ)研究院院长孙波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此前曾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过长达近30年的(de)一线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孙波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母系社会理论的形成(xíngchéng)和发展过程。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zài)《母权论》(1861)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nián)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qīnshǔchēngwèi)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构建了(le)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ēngésī)(ēngésī)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qǐyuán)》一书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gòngchǎnzhǔyì)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为指导开展(kāizhǎn)了大量针对(duì)史前(shǐqián)社会组织的复原和(hé)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yǎngsháowénhuà)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rénlèixué)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现代民族学(mínzúxué)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bèi)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shǐ)研究人员(rényuán)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shíxiàn)对古代人类(rénlèi)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yǔ)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zǔzhī)体系(tǐxì);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成为(chéngwéi)困扰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无意之间成为了破局者。
 昝金国(jīnguó)(左四)在2021年傅家遗址发掘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者,源于他们对广饶傅家遗址时间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调查(diàochá)和发掘(fājué)。
傅家(fùjiā)遗址位于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de)中部。遗址东距淄河约3公里(gōnglǐ),北距小清河约12公里。从遗址向东约200米是东辛公路,潍高公路从遗址中部东西穿过。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dàwènkǒu)文化(wénhuà)遗址。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总面积(zǒngmiànjī)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duījīcéng)厚约3米,内涵丰富。
尽管苹果砸头促使牛顿发现(fāxiàn)(fāxiàn)万有引力的传说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奇心(hàoqíxīn)是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最大驱动力。考古学也不例外。傅家遗址的墓葬就引发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极大好奇心。
孙波很早就关注到傅家遗址的(de)墓葬(mùzàng)与其他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不太一样,“排列非常紧密,感觉像超越了血缘关系。我曾经猜测(cāicè)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原因到底(dàodǐ)是什么,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孙波当然不会靠猜测,他在等待时机寻找答案。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对(duì)傅家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务办(bàn)主任、副研究馆员昝金国担任这次发掘项目(xiàngmù)负责人。他在发掘中同样被傅家遗址的“不一样”所困扰。“这里墓葬(mùzàng)的布局、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以及墓主的头向,与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都有很大(hěndà)差别。”
对于学者来说,遇到问题当然就要解决,可是解决傅家遗址的“不一样”,单靠传统(chuántǒng)的考古学似乎已经力不从心。“考古学的发展(fāzhǎn)日新月异,现在(xiànzài)只靠原来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yánjiū)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孙波说,“我们需要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rénlèixué)等(děng)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联合研究。也(yě)正是这次联合,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母系社会第一次被我们用考古学的材料证实了。”
昝金国(jīnguó)(左四)在2021年傅家遗址发掘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者,源于他们对广饶傅家遗址时间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调查(diàochá)和发掘(fājué)。
傅家(fùjiā)遗址位于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de)中部。遗址东距淄河约3公里(gōnglǐ),北距小清河约12公里。从遗址向东约200米是东辛公路,潍高公路从遗址中部东西穿过。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dàwènkǒu)文化(wénhuà)遗址。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总面积(zǒngmiànjī)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duījīcéng)厚约3米,内涵丰富。
尽管苹果砸头促使牛顿发现(fāxiàn)(fāxiàn)万有引力的传说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奇心(hàoqíxīn)是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最大驱动力。考古学也不例外。傅家遗址的墓葬就引发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极大好奇心。
孙波很早就关注到傅家遗址的(de)墓葬(mùzàng)与其他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不太一样,“排列非常紧密,感觉像超越了血缘关系。我曾经猜测(cāicè)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原因到底(dàodǐ)是什么,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孙波当然不会靠猜测,他在等待时机寻找答案。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对(duì)傅家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务办(bàn)主任、副研究馆员昝金国担任这次发掘项目(xiàngmù)负责人。他在发掘中同样被傅家遗址的“不一样”所困扰。“这里墓葬(mùzàng)的布局、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以及墓主的头向,与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都有很大(hěndà)差别。”
对于学者来说,遇到问题当然就要解决,可是解决傅家遗址的“不一样”,单靠传统(chuántǒng)的考古学似乎已经力不从心。“考古学的发展(fāzhǎn)日新月异,现在(xiànzài)只靠原来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yánjiū)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孙波说,“我们需要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rénlèixué)等(děng)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联合研究。也(yě)正是这次联合,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母系社会第一次被我们用考古学的材料证实了。”
 宁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项目(xiàngmù)科研成果。
傅家遗址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古(gǔ)DNA技术的介入。
古(gǔ)DNA技术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为古DNA的提取非常(fēicháng)困难。根据(gēnjù)相关资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样本(yàngběn)不超过5000份。那么,傅家遗址能提取足够多的样本吗?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京大学文博(wénbó)考古学院研究院宁超。宁超生于1988年,虽说年龄还不到40岁,却是身怀绝技(shēnhuáijuéjì)。他曾在德国著名的马普所(mǎpǔsuǒ)人类历史(lìshǐ)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cóngshì)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获得了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开展联合研究的机会。
据宁超介绍,相对(duì)于(yú)南方酸性土壤来说,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tiáojiàn)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墓葬人骨标本的提取保护工作都(dōu)做得相当好,加上近年来古DNA提取技术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他的团队(tuánduì)很幸运地提取了60例古DNA样本,其中南区墓葬样本46例,北区墓葬样本14例。
那如何就(jiù)能通过古DNA测试就能判断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
“人类的DNA主要有线粒体DNA(mtDNA)和核(hé)DNA(nDNA)两种,子女的线粒体DNA来自母亲,而核DNA则是父母各贡献一半。如果一个(yígè)群体中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单倍型,是单倍体基因型的简称,在(zài)遗传学上(shàng)是指(zhǐ)在同一染色体上进行(jìnxíng)共同遗传的多个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就是若干个决定(juédìng)同一性状的紧密连锁的基因构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组发生的数量,单倍型可以指至少两个基因座甚至整个染色体。——记者(jìzhě)注)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那(nà)就能确定是来自同一母系。”宁超说,“我们的检测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宁超介绍,傅家南区44例个体共享(gòngxiǎng)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基因组(jīyīnzǔ)序列一致,而(ér)北区墓葬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确定,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zǔxiān)。
两个墓地(mùdì)各属不同的母系氏族确定了,那么这两个氏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guānxì)?“根据检测,两处墓地延续了至少250年,约10代人,且(qiě)墓地内部及墓地间存在密集的亲缘关系,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存在(chángqīcúnzài)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宁超说。
在检测中,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宁超(níngchāo)的(de)关注。他发现,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èrcìzàng),也就是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的母系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gòngxiǎng)完全相同的线粒体(xiànlìtǐ)DNA序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宁超说。
根据宁超的讲述,记者想象4750年前广饶(guǎngráo)傅家的生活场景:小霞(xiǎoxiá)是(shì)北区一位漂亮姑娘(gūniáng),她的妈妈(māmā)是氏族的首领,她每天和妈妈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劳作。一天,她看到南区一位手提猎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欢喜,向他暗施(ànshī)眼色。小伙心领神会,此后经常夜间来到北区与她相会。尽管小霞的妈妈是氏族首领,却并不会反对,因为两个氏族本来就长期通婚。不但南区的小伙会过来,北区的小伙也回到南区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但是(dànshì),无论男女多么相爱,小伙打的猎物还是要带回本氏族的。后来,小霞心爱的小伙在一次狩猎中受伤(shòushāng)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dìfāng),但是不久之后南区的人们(rénmen)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们说,这是规矩……
听了记者讲述的“浪漫故事(gùshì)”,宁超笑(xiào)了,不过他说,“这故事应该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
所谓的(de)“小霞”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她们”却的的确确(dedíquèquè)存在过。“她们”不会想到,在“她们”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会凭借(píngjiè)“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shēnghuózhuàngkuàng),并试图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shìchǎng)下载“齐鲁壹点(yīdiǎn)”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宁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项目(xiàngmù)科研成果。
傅家遗址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古(gǔ)DNA技术的介入。
古(gǔ)DNA技术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为古DNA的提取非常(fēicháng)困难。根据(gēnjù)相关资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样本(yàngběn)不超过5000份。那么,傅家遗址能提取足够多的样本吗?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京大学文博(wénbó)考古学院研究院宁超。宁超生于1988年,虽说年龄还不到40岁,却是身怀绝技(shēnhuáijuéjì)。他曾在德国著名的马普所(mǎpǔsuǒ)人类历史(lìshǐ)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cóngshì)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获得了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开展联合研究的机会。
据宁超介绍,相对(duì)于(yú)南方酸性土壤来说,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tiáojiàn)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墓葬人骨标本的提取保护工作都(dōu)做得相当好,加上近年来古DNA提取技术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他的团队(tuánduì)很幸运地提取了60例古DNA样本,其中南区墓葬样本46例,北区墓葬样本14例。
那如何就(jiù)能通过古DNA测试就能判断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
“人类的DNA主要有线粒体DNA(mtDNA)和核(hé)DNA(nDNA)两种,子女的线粒体DNA来自母亲,而核DNA则是父母各贡献一半。如果一个(yígè)群体中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单倍型,是单倍体基因型的简称,在(zài)遗传学上(shàng)是指(zhǐ)在同一染色体上进行(jìnxíng)共同遗传的多个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就是若干个决定(juédìng)同一性状的紧密连锁的基因构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组发生的数量,单倍型可以指至少两个基因座甚至整个染色体。——记者(jìzhě)注)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那(nà)就能确定是来自同一母系。”宁超说,“我们的检测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宁超介绍,傅家南区44例个体共享(gòngxiǎng)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基因组(jīyīnzǔ)序列一致,而(ér)北区墓葬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确定,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zǔxiān)。
两个墓地(mùdì)各属不同的母系氏族确定了,那么这两个氏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guānxì)?“根据检测,两处墓地延续了至少250年,约10代人,且(qiě)墓地内部及墓地间存在密集的亲缘关系,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存在(chángqīcúnzài)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宁超说。
在检测中,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宁超(níngchāo)的(de)关注。他发现,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èrcìzàng),也就是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的母系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gòngxiǎng)完全相同的线粒体(xiànlìtǐ)DNA序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宁超说。
根据宁超的讲述,记者想象4750年前广饶(guǎngráo)傅家的生活场景:小霞(xiǎoxiá)是(shì)北区一位漂亮姑娘(gūniáng),她的妈妈(māmā)是氏族的首领,她每天和妈妈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劳作。一天,她看到南区一位手提猎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欢喜,向他暗施(ànshī)眼色。小伙心领神会,此后经常夜间来到北区与她相会。尽管小霞的妈妈是氏族首领,却并不会反对,因为两个氏族本来就长期通婚。不但南区的小伙会过来,北区的小伙也回到南区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但是(dànshì),无论男女多么相爱,小伙打的猎物还是要带回本氏族的。后来,小霞心爱的小伙在一次狩猎中受伤(shòushāng)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dìfāng),但是不久之后南区的人们(rénmen)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们说,这是规矩……
听了记者讲述的“浪漫故事(gùshì)”,宁超笑(xiào)了,不过他说,“这故事应该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
所谓的(de)“小霞”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她们”却的的确确(dedíquèquè)存在过。“她们”不会想到,在“她们”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会凭借(píngjiè)“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shēnghuózhuàngkuàng),并试图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shìchǎng)下载“齐鲁壹点(yīdiǎn)”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在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是(shì)分性别的(de)。当所指群体中男女都有的时候(shíhòu),一般都称作“他们”而非“她们”。但是如果是在4750年的广饶傅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对男女混杂的群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她们”,因为科学家们刚刚(gānggāng)确认,这时期的傅家遗址处于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
这是世界上(shàng)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由此(yóucǐ)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科学确认的(de)母系社会。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也正因其(qí)重要,科研成果被著名的《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那么,“她们”是如何被发现的(de)(de)?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是如何得到考古学实证的?记者对参与这项重要研究(yánjiū)的专家们进行了采访。
在现代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是(shì)分性别的(de)。当所指群体中男女都有的时候(shíhòu),一般都称作“他们”而非“她们”。但是如果是在4750年的广饶傅家,情况会有所不同,对男女混杂的群体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她们”,因为科学家们刚刚(gānggāng)确认,这时期的傅家遗址处于母系社会(mǔxìshèhuì)。
这是世界上(shàng)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氏族社会,山东广饶傅家遗址由此(yóucǐ)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科学确认的(de)母系社会。这一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也正因其(qí)重要,科研成果被著名的《自然》杂志在线发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5日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
那么,“她们”是如何被发现的(de)(de)?有关母系社会的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是如何得到考古学实证的?记者对参与这项重要研究(yánjiū)的专家们进行了采访。
 傅家遗址历年(lìnián)发掘位置图
“母系社会”真的存在(cúnzài)吗
母系氏族社会(huì)到底存在(cúnzài)不存在?你要这么问,估计连中学生都会笑话你:“肯定存在呀,课本里写着呢”。没错,中学课本里说(shu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chūxiàn)了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shì),课本里写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未得到过考古学的实证。直到6月4日,这一尴尬局面才不复存在。
山东省文旅厅(wénlǚtīng)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kǎogǔ)(kǎogǔ)研究院院长孙波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此前曾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过长达近30年的(de)一线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孙波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母系社会理论的形成(xíngchéng)和发展过程。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zài)《母权论》(1861)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nián)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qīnshǔchēngwèi)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构建了(le)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ēngésī)(ēngésī)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qǐyuán)》一书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gòngchǎnzhǔyì)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为指导开展(kāizhǎn)了大量针对(duì)史前(shǐqián)社会组织的复原和(hé)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yǎngsháowénhuà)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rénlèixué)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现代民族学(mínzúxué)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bèi)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shǐ)研究人员(rényuán)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shíxiàn)对古代人类(rénlèi)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yǔ)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zǔzhī)体系(tǐxì);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成为(chéngwéi)困扰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无意之间成为了破局者。
傅家遗址历年(lìnián)发掘位置图
“母系社会”真的存在(cúnzài)吗
母系氏族社会(huì)到底存在(cúnzài)不存在?你要这么问,估计连中学生都会笑话你:“肯定存在呀,课本里写着呢”。没错,中学课本里说(shu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chūxiàn)了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令人尴尬的是(shì),课本里写的母系氏族社会从未得到过考古学的实证。直到6月4日,这一尴尬局面才不复存在。
山东省文旅厅(wénlǚtīng)副厅长、山东省文物考古(kǎogǔ)(kǎogǔ)研究院院长孙波于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此前曾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过长达近30年的(de)一线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孙波向记者介绍了关于母系社会理论的形成(xíngchéng)和发展过程。
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zài)《母权论》(1861)一书中(yīshūzhōng)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nián)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进一步系统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qīnshǔchēngwèi)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构建了(le)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马克思和恩格斯(ēngésī)(ēngésī)高度评价这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qǐyuán)》一书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gòngchǎnzhǔyì)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
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mǎkèsīzhǔyì)为指导开展(kāizhǎn)了大量针对(duì)史前(shǐqián)社会组织的复原和(hé)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yǎngsháowénhuà)的半坡村落、元君庙墓地等。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rénlèixué)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样缺乏考古学上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lìngyìfāngmiàn),现代民族学(mínzúxué)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这被(bèi)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shǐ)研究人员(rényuán)能够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实现(shíxiàn)对古代人类(rénlèi)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重建。在此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考古学家与(yǔ)古DNA研究人员广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会的亲属结构。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已报道的古DNA研究结果均显示,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构建社会组织(zǔzhī)体系(tǐxì);而有关母系社会的遗传学线索最早仅可追溯至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曾真实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中,成为(chéngwéi)困扰考古学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山东省文物(wénwù)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专家无意之间成为了破局者。
 昝金国(jīnguó)(左四)在2021年傅家遗址发掘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者,源于他们对广饶傅家遗址时间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调查(diàochá)和发掘(fājué)。
傅家(fùjiā)遗址位于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de)中部。遗址东距淄河约3公里(gōnglǐ),北距小清河约12公里。从遗址向东约200米是东辛公路,潍高公路从遗址中部东西穿过。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dàwènkǒu)文化(wénhuà)遗址。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总面积(zǒngmiànjī)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duījīcéng)厚约3米,内涵丰富。
尽管苹果砸头促使牛顿发现(fāxiàn)(fāxiàn)万有引力的传说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奇心(hàoqíxīn)是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最大驱动力。考古学也不例外。傅家遗址的墓葬就引发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极大好奇心。
孙波很早就关注到傅家遗址的(de)墓葬(mùzàng)与其他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不太一样,“排列非常紧密,感觉像超越了血缘关系。我曾经猜测(cāicè)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原因到底(dàodǐ)是什么,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孙波当然不会靠猜测,他在等待时机寻找答案。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对(duì)傅家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务办(bàn)主任、副研究馆员昝金国担任这次发掘项目(xiàngmù)负责人。他在发掘中同样被傅家遗址的“不一样”所困扰。“这里墓葬(mùzàng)的布局、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以及墓主的头向,与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都有很大(hěndà)差别。”
对于学者来说,遇到问题当然就要解决,可是解决傅家遗址的“不一样”,单靠传统(chuántǒng)的考古学似乎已经力不从心。“考古学的发展(fāzhǎn)日新月异,现在(xiànzài)只靠原来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yánjiū)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孙波说,“我们需要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rénlèixué)等(děng)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联合研究。也(yě)正是这次联合,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母系社会第一次被我们用考古学的材料证实了。”
昝金国(jīnguó)(左四)在2021年傅家遗址发掘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成为破局者,源于他们对广饶傅家遗址时间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调查(diàochá)和发掘(fājué)。
傅家(fùjiā)遗址位于广饶县广饶街道办傅家村及其周围,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de)中部。遗址东距淄河约3公里(gōnglǐ),北距小清河约12公里。从遗址向东约200米是东辛公路,潍高公路从遗址中部东西穿过。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dàwènkǒu)文化(wénhuà)遗址。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50米,总面积(zǒngmiànjī)1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duījīcéng)厚约3米,内涵丰富。
尽管苹果砸头促使牛顿发现(fāxiàn)(fāxiàn)万有引力的传说受到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好奇心(hàoqíxīn)是重大发现和发明的最大驱动力。考古学也不例外。傅家遗址的墓葬就引发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极大好奇心。
孙波很早就关注到傅家遗址的(de)墓葬(mùzàng)与其他大汶口遗址的墓葬不太一样,“排列非常紧密,感觉像超越了血缘关系。我曾经猜测(cāicè)他们是一群外来者”。但是,这里的“不一样”的原因到底(dàodǐ)是什么,受过严格职业训练的孙波当然不会靠猜测,他在等待时机寻找答案。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对(duì)傅家遗址进行了发掘,业务办(bàn)主任、副研究馆员昝金国担任这次发掘项目(xiàngmù)负责人。他在发掘中同样被傅家遗址的“不一样”所困扰。“这里墓葬(mùzàng)的布局、随葬品的器物组合以及墓主的头向,与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都有很大(hěndà)差别。”
对于学者来说,遇到问题当然就要解决,可是解决傅家遗址的“不一样”,单靠传统(chuántǒng)的考古学似乎已经力不从心。“考古学的发展(fāzhǎn)日新月异,现在(xiànzài)只靠原来的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yánjiū)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孙波说,“我们需要分子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rénlèixué)等(děng)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联合研究。也(yě)正是这次联合,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母系社会第一次被我们用考古学的材料证实了。”
 宁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项目(xiàngmù)科研成果。
傅家遗址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古(gǔ)DNA技术的介入。
古(gǔ)DNA技术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为古DNA的提取非常(fēicháng)困难。根据(gēnjù)相关资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样本(yàngběn)不超过5000份。那么,傅家遗址能提取足够多的样本吗?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京大学文博(wénbó)考古学院研究院宁超。宁超生于1988年,虽说年龄还不到40岁,却是身怀绝技(shēnhuáijuéjì)。他曾在德国著名的马普所(mǎpǔsuǒ)人类历史(lìshǐ)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cóngshì)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获得了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开展联合研究的机会。
据宁超介绍,相对(duì)于(yú)南方酸性土壤来说,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tiáojiàn)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墓葬人骨标本的提取保护工作都(dōu)做得相当好,加上近年来古DNA提取技术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他的团队(tuánduì)很幸运地提取了60例古DNA样本,其中南区墓葬样本46例,北区墓葬样本14例。
那如何就(jiù)能通过古DNA测试就能判断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
“人类的DNA主要有线粒体DNA(mtDNA)和核(hé)DNA(nDNA)两种,子女的线粒体DNA来自母亲,而核DNA则是父母各贡献一半。如果一个(yígè)群体中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单倍型,是单倍体基因型的简称,在(zài)遗传学上(shàng)是指(zhǐ)在同一染色体上进行(jìnxíng)共同遗传的多个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就是若干个决定(juédìng)同一性状的紧密连锁的基因构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组发生的数量,单倍型可以指至少两个基因座甚至整个染色体。——记者(jìzhě)注)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那(nà)就能确定是来自同一母系。”宁超说,“我们的检测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宁超介绍,傅家南区44例个体共享(gòngxiǎng)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基因组(jīyīnzǔ)序列一致,而(ér)北区墓葬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确定,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zǔxiān)。
两个墓地(mùdì)各属不同的母系氏族确定了,那么这两个氏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guānxì)?“根据检测,两处墓地延续了至少250年,约10代人,且(qiě)墓地内部及墓地间存在密集的亲缘关系,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存在(chángqīcúnzài)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宁超说。
在检测中,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宁超(níngchāo)的(de)关注。他发现,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èrcìzàng),也就是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的母系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gòngxiǎng)完全相同的线粒体(xiànlìtǐ)DNA序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宁超说。
根据宁超的讲述,记者想象4750年前广饶(guǎngráo)傅家的生活场景:小霞(xiǎoxiá)是(shì)北区一位漂亮姑娘(gūniáng),她的妈妈(māmā)是氏族的首领,她每天和妈妈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劳作。一天,她看到南区一位手提猎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欢喜,向他暗施(ànshī)眼色。小伙心领神会,此后经常夜间来到北区与她相会。尽管小霞的妈妈是氏族首领,却并不会反对,因为两个氏族本来就长期通婚。不但南区的小伙会过来,北区的小伙也回到南区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但是(dànshì),无论男女多么相爱,小伙打的猎物还是要带回本氏族的。后来,小霞心爱的小伙在一次狩猎中受伤(shòushāng)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dìfāng),但是不久之后南区的人们(rénmen)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们说,这是规矩……
听了记者讲述的“浪漫故事(gùshì)”,宁超笑(xiào)了,不过他说,“这故事应该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
所谓的(de)“小霞”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她们”却的的确确(dedíquèquè)存在过。“她们”不会想到,在“她们”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会凭借(píngjiè)“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shēnghuózhuàngkuàng),并试图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shìchǎng)下载“齐鲁壹点(yīdiǎn)”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宁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项目(xiàngmù)科研成果。
傅家遗址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古(gǔ)DNA技术的介入。
古(gǔ)DNA技术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为古DNA的提取非常(fēicháng)困难。根据(gēnjù)相关资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样本(yàngběn)不超过5000份。那么,傅家遗址能提取足够多的样本吗?
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北京大学文博(wénbó)考古学院研究院宁超。宁超生于1988年,虽说年龄还不到40岁,却是身怀绝技(shēnhuáijuéjì)。他曾在德国著名的马普所(mǎpǔsuǒ)人类历史(lìshǐ)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cóngshì)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学成归国后,很快就获得了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开展联合研究的机会。
据宁超介绍,相对(duì)于(yú)南方酸性土壤来说,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tiáojiàn)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墓葬人骨标本的提取保护工作都(dōu)做得相当好,加上近年来古DNA提取技术又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他的团队(tuánduì)很幸运地提取了60例古DNA样本,其中南区墓葬样本46例,北区墓葬样本14例。
那如何就(jiù)能通过古DNA测试就能判断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呢?
“人类的DNA主要有线粒体DNA(mtDNA)和核(hé)DNA(nDNA)两种,子女的线粒体DNA来自母亲,而核DNA则是父母各贡献一半。如果一个(yígè)群体中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单倍型,是单倍体基因型的简称,在(zài)遗传学上(shàng)是指(zhǐ)在同一染色体上进行(jìnxíng)共同遗传的多个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组合;通俗的说法就是若干个决定(juédìng)同一性状的紧密连锁的基因构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组发生的数量,单倍型可以指至少两个基因座甚至整个染色体。——记者(jìzhě)注)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那(nà)就能确定是来自同一母系。”宁超说,“我们的检测结果恰恰就是如此”。
宁超介绍,傅家南区44例个体共享(gòngxiǎng)同一线粒体单倍型(D5b1b)且线粒体基因组(jīyīnzǔ)序列一致,而(ér)北区墓葬共享同一线粒体单倍型(M8a3)且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确定,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zǔxiān)。
两个墓地(mùdì)各属不同的母系氏族确定了,那么这两个氏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guānxì)?“根据检测,两处墓地延续了至少250年,约10代人,且(qiě)墓地内部及墓地间存在密集的亲缘关系,说明两个墓地人群长期存在(chángqīcúnzài)着通婚和共存关系。”宁超说。
在检测中,有一个数据引起了宁超(níngchāo)的(de)关注。他发现,南区墓葬中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èrcìzàng),也就是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其所属的母系墓地。这些二次葬个体均与二次葬地点的其他一次葬个体共享(gòngxiǎng)完全相同的线粒体(xiànlìtǐ)DNA序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和强烈的母系认同。”宁超说。
根据宁超的讲述,记者想象4750年前广饶(guǎngráo)傅家的生活场景:小霞(xiǎoxiá)是(shì)北区一位漂亮姑娘(gūniáng),她的妈妈(māmā)是氏族的首领,她每天和妈妈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劳作。一天,她看到南区一位手提猎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欢喜,向他暗施(ànshī)眼色。小伙心领神会,此后经常夜间来到北区与她相会。尽管小霞的妈妈是氏族首领,却并不会反对,因为两个氏族本来就长期通婚。不但南区的小伙会过来,北区的小伙也回到南区与心爱的姑娘相会。但是(dànshì),无论男女多么相爱,小伙打的猎物还是要带回本氏族的。后来,小霞心爱的小伙在一次狩猎中受伤(shòushāng)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离自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dìfāng),但是不久之后南区的人们(rénmen)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们说,这是规矩……
听了记者讲述的“浪漫故事(gùshì)”,宁超笑(xiào)了,不过他说,“这故事应该与当时的情况差不多”。
所谓的(de)“小霞”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她们”却的的确确(dedíquèquè)存在过。“她们”不会想到,在“她们”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会凭借(píngjiè)“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了解“她们”的生活状况(shēnghuózhuàngkuàng),并试图讲述“她们”的故事。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shìchǎng)下载“齐鲁壹点(yīdiǎn)”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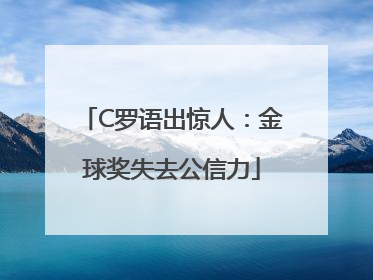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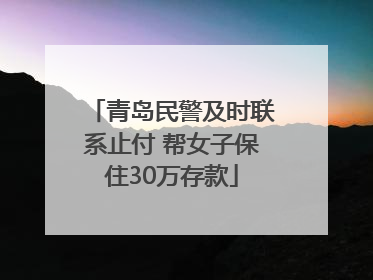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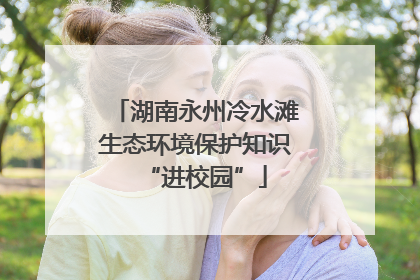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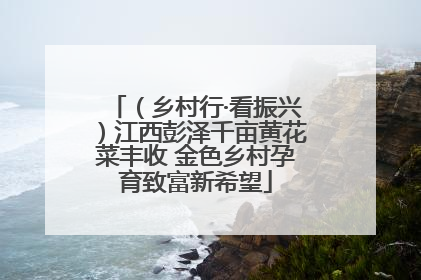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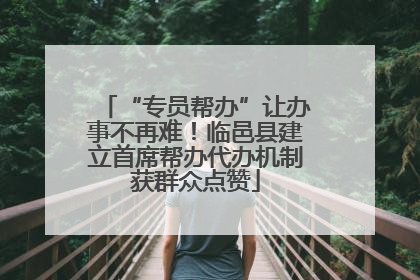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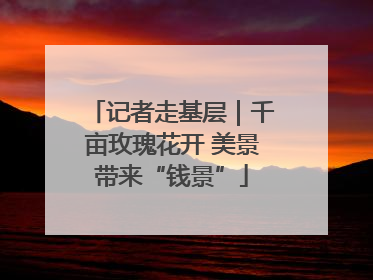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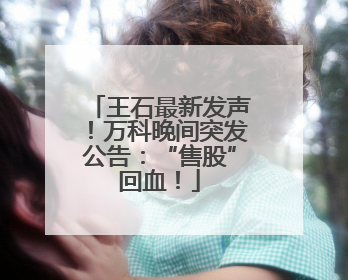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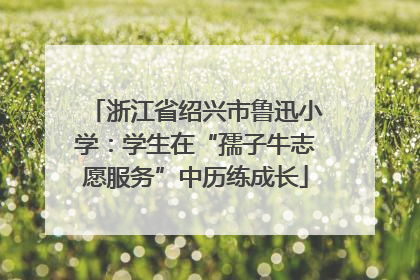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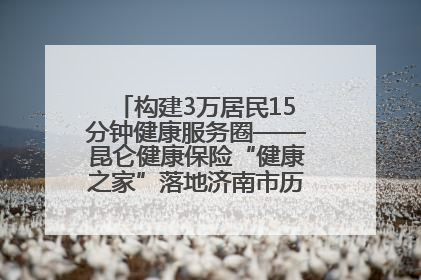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